中國代駕行業多年來寄居監管真空的現實,并沒有妨礙“代駕”群體的野蠻生長,他們憑借與消費者之間達成的“契約”守護著自己的“飯碗”。無論代駕模式如何變化,但它或多或少給代駕人員、消費者乃至整個行業帶來了安全感。然而,市場上基于這一紙“契約”的“代駕”模式層出不窮,卻并沒有展示出一個新興行業應展示給消費者的信任感,這種信任危機正在成為“代駕”成長的天花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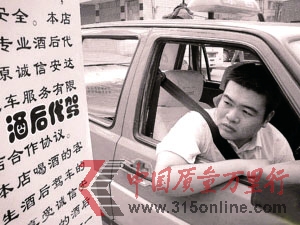
每逢節假日城市各種聚會酒宴正酣,也恰是代駕江湖最熱鬧的時候。
18時整,是代駕司機張建明開始忙活兒的時候。他接到還在公司——北京市海淀區車公莊西路值班的調度員小吳的電話,他掛掉電話,穿上工裝佩戴好工牌,拎上工包,從朝陽的家里出發到達小吳電話中說的飯店。張建明找到客戶,出示了駕駛證和一份服務協議,“這份公司統一印制的協議,印有‘代駕服務行程單’和‘代駕服務的質量管理規范’,是我們雙方的唯一保障。”客戶閱讀的空檔,他仔細檢查車身有無刮痕,并確認汽車的“三險”,核實到達地點與約定費用,待客戶在協議書上簽字后上車,張建明將車順利啟動后駛出了停車場。
“大多數客戶起初都會不放心,從他們坐上車到行駛一公里左右就是對我們的考察期,起步、掉頭、換擋……得流暢到位。”
一路上,操一口“京腔”的張建明征求了客戶的路線要求,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議,考慮到客戶喝了酒,張建明將車速放慢。沒一會兒,車廂里熱鬧起來,客戶與他開始隨意聊天。“客戶足夠信任你時,有人會跟你聊很多,大多數人習慣休息,‘我先睡會兒,到了叫我’。”到達目的地,張建明還回鑰匙下車。他請客戶下車檢查車況,客戶放心的直接付費并在確認單上簽字。待客戶離開,他記錄下服務終止的間并告知小吳。
這樣的一筆單子和整套服務流程,對已在北京奔奧安達汽車駕駛服務有限公司工作了4個年頭的張建明來說,再熟悉不過。“公司有部分兼職的代駕員,平時基本只拉一單,最近估計得每天兩單才能收工。我們這些專職代駕,平時兩單,現在也要趕著第三單了,有幾次甚至到凌晨三點才能坐上公司負責接送代駕人員的班車回家。”
跟張建明一樣,在北京市,手持一紙“契約”養家糊口的專業代駕僅奔奧安達就有220人,涉及代駕服務項目的公司就有近百家。然而,無論在《中國職業分類大典》還是在《國民經濟行業分類》,卻根本找不到對“代駕”的描述,更別提其行業和職業標準了。代駕,成為中國傳統七十二行外的第七十三行。
熬出來的“正規軍”
2008年北京奧運會閉幕不久,待業在家的張建明得知一個朋友因醉駕進了拘留所,朋友聚會開車喝酒不可避免,那么,是否能夠找到其他的方式避免醉駕呢?他覺得某天在報紙上發現的“代駕”新名詞必定是一個商機。而他的這一想法,與后來成為他老板的奔奧安達公司董事長何進不謀而合。
不過,何進看到“代駕”市場是2003年10月28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取代了施行長達15年之久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管理條例》。何進注意到第九十一條的規定,他發現酒后駕車不僅違法,而且執法力度加大了。那年年底,他憑借多年積累的10萬元注冊資本申請注冊代駕公司時遭到了拒絕,最后不得不注冊了“汽車駕駛服務”。
當時,市場上雖然已有了汽車代駕這項業務,但想要做專業汽車代駕公司,何進還是頭一家。酒后代駕像欣賞電影和享受腳底按摩等服務一樣,接受酒后代駕的人享有了服務,酒醒后發現“車還是自己的車,駕駛者還是自己”,但它又不像別的服務,車是貴重物品,不可預知的重大風險如影隨形。“別人對你根本不了解,誰敢用你?”
事實印證了何進的顧慮。開業當天,他們就吃了零單,接下來的半年時間也一直在虧損。“在執法不嚴的情況下,大家都是酒后駕車,但代價和后果是巨大并且慘痛的。”直到2004年5月1日新交通法正式實施后,情況才稍有好轉。和許多創業者一樣,何進的代駕公司發展的并不順利,“公司成立到2006年是最難熬的三年,每天的業務量不到10單,而企業運營需要的各項費用有增無減。”
公司遲遲沒有行業歸屬,車主對代駕并不熟悉,業務增長更多依賴客戶口碑,而市場總是不溫不火,要想給市場加溫,需要更多的前期投入,對剛起步的奔奧安達來說,這無疑是難上加難。“正是置身于低門檻的行業和僅能憑口碑創造效益的‘三年’,增加了我對建立一支代駕正規軍的決心。”
直到2007年全國加大對“醉駕”執法力度時,對許多擁有代駕業務的公司,才有了些許轉機。憑借已相對成熟的經營模式和規范服務,奔奧安達先后在南京、武漢、南寧、天津建立了分公司。
2011年5月1日,中國正式將酒駕列入刑法條例,更是給代駕業務注射了一劑“強心針”,可以說算是迎來了“酒后代駕”的春天。公司的初具規模和管理經驗的深度積淀,讓何進有了一些欣慰,“很明顯,就是訂單量一直在翻倍,調度很忙,駕駛人員變得緊張。”代駕人員也在增加,在奔奧安達,年齡在30-50歲之間,駕齡在8年以上的北京本地人,經過公司的面試、路考和嚴格培訓后陸續上崗。公司將代駕人員劃分為八個分隊時,張建明當上了“朝陽二隊”的隊長,負責朝陽近30個代駕人員的日常管理,“公司業務量也由進公司的60-70單已經翻番。”
一路走來,代駕服務協議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p#副標題#e#
一直呼吁代駕“被管”的何進,可以稱得上是擬定這一“契約”的開創者。他始終堅持,行業的發展,取決于服務的規范化和業務的規模化,“只有這樣,才能贏得消費者的口碑。近幾年,公司吸納了200多家金融機構和大企業會員,獲得的服務質量方面的榮譽,正得益于此。”奔奧安達作為專業的代駕公司,除了在代駕人員準入機制和代駕服務價格標準、突破撥打400-628-6288免費服務電話的傳統方式,創新綜合性服務平臺等方面下功夫之外,這一紙“契約”——服務協議正是作為規范整個行業的入場券,也在一定程度上給消費者吃了“定心丸”。無論代駕模式如何變化,但它或多或少給代駕人員、消費者乃至整個行業帶來了安全感。
“雜牌軍”的沒落
另一方面,這一“契約”也成為了代駕“雜牌軍”沒落的催化劑。截止2012年5月,“醉駕入刑”施行一年,全國共查處酒駕行為35.4萬次,同比下降了4成,酒駕呈現下降趨勢。但中國人從“車是身份的象征”的觀念到“無酒不成席”的社交禮節和“酒逢知己千杯少”的人際關系體現,無不將“酒”和“車”緊密聯系起來。
一直以來,“代駕”作為一個新興的城市服務行業在野蠻生長。2004年7月,湖南長沙首家注冊代駕公司誕生;2005年,南京市出現首家代駕公司;2006年8月,浙江第一家代駕公司上路;2007年初,云南昆明開始出現代駕公司;2008年10月,河南鄭州第一家“代駕公司”成立;2009年9月,上海市工商局開始受理“代駕公司”登記注冊申請;2010年初,廣東首家代駕公司成立;2012年5月,重慶出臺首個代駕企業規范標準……面對這種局面,何進和同行們顯得十分憂愁。但這種憂愁并不是因為市場在逐步被瓜分,而是各種標準參差不齊的情況下,這個“大蛋糕”未得到充分消化。按北京500萬輛自駕車計算,僅10%的車主每月一次代駕需求,一次花費100元,一年全市代駕收入將達6億元。按照代價行業如今的規模和收入狀況,只能算“冰山一角”,要說被消化的部分也是在囫圇吞棗。幾年下來,何進就曾眼睜睜地見識過一些代駕企業的夭折。
究其原因,除了人們的消費習慣還有待培養,他們歸因于行業運營環境的“無名無份”。這個行為超前、法律滯后的新行業里,行業無主管單位、無準入門檻、無統一收費標準的“三無”現狀持續了近十年,讓原本被看好的市場始終處于尷尬的境地。這種停滯不前的行業歸屬問題,也易使消費者產生交通事故、財物丟失、服務內容及質量糾紛、合同效力糾紛、人身傷害糾紛等方面的顧慮。拿奔奧公司來說,八年間承接了220萬元酒后代駕業務并無一單糾紛,也形成了業內較為成熟的經營管理模式,可該公司的工商營業執照上仍只被允許是“汽車駕駛服務”,代駕兩個字從來沒出現過。
更為嚴重的現象是,低行業門檻導致了代駕行業的“雜牌軍”叢生。許多從事代駕業務的公司,有的缺乏基本的人員培訓機制,有的大多數為兼職人員,有的外地司機占了大多數;數不清的“黑戶”在論壇等發帖尋求代駕機會……他們的信息大多出現在網頁或酒吧的廣告攤位上,消費者很難核實其身份與駕齡的真實性,更無協議和風險規避措施,這種“黑代駕”憑借口頭承諾與消費者達成協議,導致的嚴重后果屢屢給行業的發展帶來了隱憂。
代駕久了,張建明在與客戶的聊天中多少聽過這些“雜牌軍”,“接觸的客戶中,有的就受過‘黑代駕’的當,因為是口頭協議,價格、安全都沒法保障,有代駕人員甚至給顧客五花八門的推銷。聽到他們在接受我們的服務后說,‘還是你們公司司機的水平比較高’。”消費者的評價讓張建明和他的同事們會覺得很自豪。
“新式軍”受寵隱憂
隨著人們生活方式的不斷變化,手機客戶端代駕應運而生。消費者只需要下載并打開一個手機客戶端,就會直接顯示離消費者最近的5名代駕者信息,司機姓名、登記照、籍貫、駕齡、身份證號、駕駛證、聯系方式以及離本人的距離等一應俱全,點擊一位空閑狀態的代駕者頭像預約,20分鐘左右就能到達現場。
這一模式無疑突破了傳統代駕公司必須通過呼叫中心才能提供代駕服務的瓶頸,并以39元(含10公里內)的較低代駕起步費用獲得了良好的市場反應和用戶口碑。
這種低于市場平均水平的信息費,保證了代駕人員的收入,成為吸引廣大代駕人員與其合作的重要因素,也成為這種“新式軍”受寵的關鍵原因。張建明的同事們也聽過這種新潮模式,“這種模式節約了司機和客戶的時間,確實給消費者帶來了方便。特別像目前代駕人員調度比較緊張的時候。”據一家名為“e代駕”的內部人士透露,其在北京的訂單量每天大約在600-700單之間,上海每天訂單量為100單左右。
面對“新式軍”的受寵,在風云變幻的代駕江湖摸爬滾打多年的何進深知這“契約”背后的隱憂。在人身財產安全和時間、金錢的權衡和博弈中,多數消費者也極易忽視最重要的一點,這看似規范的流程背后,存在很大的風險防范漏洞。盡管和規范的代駕服務一樣,手機客戶端代駕也通過《代駕委托書》與客戶形成“契約”,而且服務中也明確指出:為防止事故發生,單人或多人醉酒且無清醒同伴陪同、驗車發現存在安全隱患、客戶拒簽《代駕委托書》等三種情況,代駕者可以拒絕提供代駕服務。
容易讓我們忽視的是,這一利益鏈條上手機客戶端的開發者本質上就是“信息發布平臺”,與代駕人員之間僅是一種合作關系而并非雇傭關系。也就是說,客戶端上的代駕人員與消費者簽署的“契約”,實質上是一份車主、代駕人員和信息發布平臺的三方合同,在事故的歸責中,這一信息發布平臺僅能確保代駕人員信息的真實性。
這就意味著,無事故,消費者可樂享其服務。一旦發生事故,能夠為此項服務事故負責的,除了保險公司,就是代駕人員和消費者,超出保險公司和代駕人員的范圍,只能由消費者“埋單”。
相較之下,像張建明一樣,與代駕公司達成雇傭關系的代駕人員出示的“契約”中,代駕公司承擔車輛有責部分的賠償,且遵循先由交強險賠償,再由車輛商業險賠償的原則。如果以上兩方面賠償后仍有損失余額,則由代駕公司賠償。
這就意味著,一旦發生事故,能夠為此相對規范的代駕服務事故承擔責任的,除了保險公司,就是代駕公司。
簡而言之,在當下服務標準和服務規范良莠不齊的代駕江湖,這罩住整個行業的一紙“契約”正在不斷變形,并沒有展示出一個新興行業應展示給消費者的信任感,這種信任危機正在成為“代駕”成長的天花板。在一系列行業歸屬和規范出臺的曙光之前,代價群體、消費者仍需在這出“契約”變形記里摸爬滾打、斗智斗勇。










 京公網安備11010502034432號
京公網安備11010502034432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