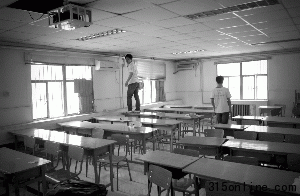屢遭性侵變得沉默寡言
我決定聽他(班主任)的。那些天我很努力很努力地學習,可是身體卻被拖垮了,不得不回家休息。后來李聽說我回家之后,打了電話給我,我沒看到,看到之后就回了他一些短信,給他打了幾次電話。
后來他開車到我家附近接我,我隨他去了他家(迫于害怕他讓我休學及戶口無法辦理和自己微弱的封建意識的情況下,不得不從)。那晚我們都喝了酒,當晚我們發生了第二次性關系,雖然我有反抗,但態度已沒第一次那么強烈(顧慮自己上學,戶籍和名聲)
直至4月6日,我和他共在一起發生了四次關系,直到我因病暈厥,去往西安看病。
在我離校期間,李多次以不該讓我去西安看病為由找我們班主任的麻煩,班主任不想我為他擔心,對自己所受的委屈只字不提,一味地給我寬心讓我安心看病。
吳曉告訴記者,遭受校長的性侵害之后,自己精神郁悶,唯有通過不停歇的學習,才能暫時忘記那可怕的夜晚。吳曉的同學對記者說,吳曉當時學習的勁頭到了近乎瘋狂的地步,每晚一兩點還躲在被窩里,借助手電筒看書,早上五點半準時起床,簡單洗漱后第一個進教室開始自習。吳曉做夢都在背單詞。超負荷的學習和內心的煩悶,讓吳曉開始變得沉默寡言,每天幾乎只吃一頓飯。
吳曉的姑姑向記者回憶道,性格開朗的侄女一月內瘦了大約十斤,回家就是睡覺,也不和姐妹們打羽毛球了,滿腹心思的樣子,飯也懶得吃。問她有何心事。吳曉直喊累了,不舒服,想一個人在床上躺會。
吳曉越來越感到困倦,頭暈,不得不請假回到距離學校一公里外的姑姑家休息。這些在吳曉看來都不算什么,她說自己最害怕聽到校長李懷松的關心電話。得知吳曉帶病上學,李便提醒吳曉的班主任應該讓吳曉看病休息,不要因此延誤吳曉的治療時機。得知吳曉在姑姑家沒去上學,李校長就會打電話來詢問病情,還會親自上門看望。而往往每次看望,吳曉說李都會示意她跟自己走。到李校長家里意味著什么,吳曉稱自己知道如果不去,校長就會命令班主任安排她去醫院檢查。她害怕學校借故讓她退學,不但會失去中考的機會,甚至會因此輟學。因為學校不會承認此前開具的自己是在校生證明的有效性,自己可能再次失去獲得戶籍的機會。
妹妹在夢中直喊快走開
“在他面前我是一個沒有靈魂的人,只剩下一副軀殼。我只希望這一切盡快結束。”在第四次從李校長家里離開時,吳曉稱自己扶著墻壁都站立不穩。最后體力不支的她被迫再次請假,回到姑姑家里。第二天,吳曉從床上摔倒在地,神志不清長達6個小時。最后被前來探望的同學發現,報告給了班主任。李懷松校長得知后,立刻前來探望,打電話叫來了救護車,并親自把吳曉從地上抱著送上了救護車。
吳曉的哥哥得知妹妹病重暈倒的消息后,連忙趕回石泉縣,帶著妹妹到西安檢查“得了什么大病”。在和妹妹相處的七八天里,哥哥發現妹妹吳曉晚上老睡得不踏實,一臉驚恐,時常在睡夢中高喊:“走開,走開。”哥哥問吳曉緣由,她推脫說自己做噩夢,掉在一片深水內,總也游不上岸。“當時也沒有想什么,也不敢往那方面想。”只是經過一系列檢查,醫生說吳曉沒病。后來哥哥再次聽到妹妹出事的消息,被教體局的人帶走了。“打電話給我媽的時候,她才告訴我說,妹妹被學校校長欺負了。”哥哥說,最擔心的事情還是發生了,但沒想到竟然是老師,還是一校之長。
懷孕了又流產了
后來我病愈可返校學習,但仍無法正常上課,李再度提出讓我休學回家休養,迫于想盡快返回學校的心態,我和學校簽訂了一份協議,協議表示在校期間如因不守學校紀律或身體原因發生任何事學校概不負責。
簽訂協議后,我返校學習期間,卻發現有了妊娠反應,一時之間陷入惶恐,不知該怎么辦。
語文老師發現了我的不良發應,建議我去做檢查,于是4月23日便去了石泉中醫醫院,用了一個假名字和年齡去了內科做檢查,檢查結果為陰性,我的心一時安定下來。可大夫卻說那個檢查結果有可能因為檢查時段的原因不準確,建議我去婦科看一下,并給我開了一些止吐的藥。
我去了婦科。大夫看了一下我的處方筆詢,問了我的癥狀后,問我要不要那個孩子,要的話就不要吃大夫開的藥,讓我一周之后再來檢查。
出了醫院我陪同學逛街買衣服,走了很久可能有些累,又吃了些冷飲,走到迎賓路附近,我感覺肚子很疼,疼痛感越來越強烈,我找到附近的公廁,進去以后,發現有許多血塊和一個顏色較深的血球排出,等已經沒有太多的血排出的時候,疼痛感已經沒有那么強烈了,就去了附近的縣醫院向醫生說明了我有出血的狀況,并未提及可能是懷孕。醫生就幫我開了一些藥。
后來我打電話咨詢了另一位醫生,提及了懷孕。她說有百分之九十的可能是流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