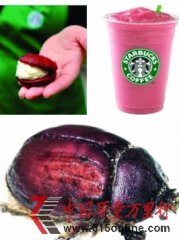病從口入誰之過
層出不窮的食品、藥品安全問題,日新月異的科技“幫兇”,這一切的根源,到底在于我國相關法律的缺失,還是無良商家利欲熏心,置法律與不顧,抑或是其他環節出現了問題?
記者—王若翰
重典能否治亂?
“《食品安全》法頒布3年以來,食品安全問題不但屢禁不止,而且愈演愈烈,現在,又擴散到藥品領域,這實在是太可怕了!既然一些無良商家一味追 逐利益最大化,道德已無法對其形成約束,那我提議,干脆制定一項‘反生命罪’‘反健康罪’,用刑法告訴不法經營者,生命應該如何被敬畏!”中國社會科學院 社會學者沈杰說。
高曉松酒駕事件,成為了中國交通安全法治理酒后駕車的一座“里程碑”。相較于治理酒駕而言,我國在對食品、藥品安全違規的懲處上,則顯得有些過于寬松,除經濟處罰外,似乎極少有企業法人因此承擔刑事責任。低廉的違規成本,同可觀的違規利益形成鮮明對比,促使經營者選擇置法律于不顧,屢屢以身試 法。
沈杰在接受《新民周刊》專訪時,提出:對食品安全問題的治理,應該拿出治理酒駕一樣從嚴的態度。采訪過程中,多位專家、學者均認為,應加大食品、藥品安全的懲處力度,沈杰更提出,應該將明知故犯的商家界定為犯罪,而不僅僅是違法。
食品、藥品并非無法可依。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楊建順告訴記者,早在1995年,我國就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衛生法》。在此基礎 上,2009年2月28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法》是適應新形勢發展的需要,為了從制度上解 決現實生活中存在的食品安全問題,更好地保證食品安全而制定的,其中確立了以食品安全風險監測和評估為基礎的科學管理制度,明確食品安全風險評估結果作為 制定、修訂食品安全標準和對食品安全實施監督管理的科學依據。
在藥品的監管上,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法》更是從2001年12月1日起便開始施行,在《藥品管理法》的第二章“藥品生產企業管理” 的第十一條中,明確要求:生產藥品所需的原料、輔料,必須符合藥用要求。而在該法案的第五章藥品管理的第四十九條“禁止生產、銷售劣藥”中也有如下字樣: “藥品成分的含量不符合國家藥品標準的,為劣藥。”在劣藥的定義中,第四項即是“直接接觸藥品的包裝材料和容器未經批準的”。
結合《藥品管理法》中的以上表述,此次“毒膠囊事件”所用的工業明膠明顯不符合第二章第十一條中“生產藥品所需的原料、輔料,必須符合藥用要求”一項,而至于是否經過監管部門的批準,卻尚無定論。
楊建順告訴記者,目前國內,無論是食品管理還是藥品管理,都已經擁有一套十分完備的法案,至于屢禁不止的視頻、藥品安全問題,絕非法律漏洞所致,實為部分經營者有法不依、鋌而走險的個人行為。
沈杰進一步指出:“一些食品、藥品生產廠家,明知其生產原料與生產手法對消費者的健康有害,卻出于降低成本等目的考慮,置消費者的生命健康于不 顧,這已不僅僅是違法的問題,而是赤裸裸的謀財害命、是犯罪,與殺人無異。只不過這個殺人的說法更隱蔽,效果更緩慢而已,更可怕的是,由于一些科學檢測手 段的局限,一些隱形的影響很有可能不會馬上顯現,而是推遲到幾十年之后,甚至是在下一代人的身上表現出來。這其實比直接的殺人更讓人覺得恐怖。”
基于以上原因考慮,沈杰認為,對于違法者,不僅應將其定性為刑事犯罪,更應該對涉案所有部門、人員予以嚴懲,將一條不法產業鏈上的所有參與者都繩之以法,以儆效尤。這樣才能使我國當下的食品、藥品安全問題得到根本的解決。
監管不力?
與之前的《食品衛生法》相比,2009年開始實行的《食品安全法》更強調了從農田到餐桌的一體化動態監管。而這其中的各個環節,其實并非一個部 門負責。楊建順舉例說明:“農場歸農業部管理,農產品加工過程中則由工商部門和其他技術監督部門介入監管,加工成成品之后又有食品藥品監督局把關。各部門 之間的分階段管理,實際上給食品安全從農田到餐桌的一體化監管設置了障礙。
近年來,對于食品、藥品的安全問題,各地開始實行地方政府統一負責制。在楊建順看來,這是一個很好的監管機制,在政府的統一部署下,各監管部門 可以無縫銜接,避免出現監管漏洞。從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監管經驗來看,由某一部門全權負責,監管到底的統一領導、協調的機制亦是成功而可取的。
在這樣“無縫銜接”的監管機制下,食品、藥品安全依舊接二連三地出現問題,對于公眾對政府監管不力的指責,楊建順解釋:“要求監管部門每天24 小時監管的想法是不現實的,監管部門不能天天盯著企業經營者不放,只能定期或不定期地對生產企業進行檢查或抽查。這樣的客觀情況,導致個別經營者鉆了監管 的空子,也是有可能的,并不能因此就把所有責任歸咎為監管不力。”
對于楊建順的觀點,同在中國人民大學的政治系教授張鳴則持有不同的態度,在接受《新民周刊》的采訪時,張鳴直言,在他看來,我國現有的監管部門 都是標準的“衙門”。“衙門雖是衙門,但都有生利的沖動。最熱衷的兩件事,一是給商家發放各種優秀標牌,組織各種評獎,最后大家你好我好,家家都是優秀。 無論哪個商家出事,到它們辦公室去看,都是一屋子的獎狀,半屋子的獎杯,還有滿抽屜的合格以及優秀證書。二是定期檢查企業的產品,查出問題,然后等企業上 門公關,公關到位,原來不合格的,就變成合格了。”換而言之,食品、藥品的安全問題,在中國之所以屢屢出錯,監管部門難辭其咎!
張鳴認為,中國在食品、藥品監管的問題上面可以借鑒國外的NGO模式,通過協會、社團、基金會、慈善信托、非營利公司或其他法人等不以營利為目 的的非政府組織,對企業加以監管。這種NGO組織具有不是政府,不靠權力驅動,同時也不是經濟體,尤其不靠經濟利益驅動,以志愿精神為原動力的特點,是公 民社會興起的一個重要標志。中國甚至可以通過嘗試邀請國外NGO參與,借鑒人家的做法,對本國的食品、藥品安全進行監管。
不法企業的保護傘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者沈杰長期以來一直倡導依法治國的國家發展方向。沈杰表示,一些地方政府,出于GDP等政績因素考慮,極有可能成為不法企業及經營者的保護傘。
在采訪中,沈杰舉例說明:“對于食品、藥品行業內的一些齷齪內幕,我們出于正常角度考慮,不法生產經營者必會受到行業內其他企業的舉報,行業協 會甚至應該將個別‘敗類’踢出此行業,以凈化整個行業氛圍,使得該行業可以得到更好的發展。而事實上恰恰相反,一些不法企業通過高科技手段實施的無良行 為,往往會讓其他企業爭相效仿。”
早在三鹿乳業三聚氰胺事件東窗事發之時,網絡企業中就曝出過這樣的傳言:“三聚氰胺在乳制品企業內部,早就是個公開的秘密,區別只在于,到底是 往奶粉中摻雜三聚氰胺,還是在三聚氰胺中添加奶粉。”更有一些企業坦言,整個行業都這么做,你若不做,成本上就要高出很多,在市場上自然無法同其他同行競 爭。此次的毒膠囊事件,亦是如此,涉及到的藥品企業既有‘修正’一類的大廠,也有其他小廠,其在藥品行業內的覆蓋范圍可見一斑。”如此看來,倒像是整個行 業逼迫企業不得不成為無良商家。
沈杰表示,基于以上因素分析,一些地方監管部門很可能在監管的過程中,充當了不法經營者的保護傘,使正規生產經營的商家舉報無門、走投無路,從而不得不選擇同流合污。
一個發展良好的行業,其本身應該擁有一定的自凈能力,個別商家的唯利是圖,影響的往往是整個行業的信譽,沒有了信譽,對于行業則是毀滅性的打 擊。所以,出于行業的整體和長遠利益考慮,行業內部會進行自我約束,自我審查,自我懲處。這樣的自凈,需要基于市場的商家自組織系統。
張鳴表示:在中國古代,商家也生產食品和藥品,那個時候,每個行業都有行會,后來還有了商會。如果哪個商家干了這種事情,又被人揭發出來,那 么,也沒有人懲罰他們,行會知會大家一聲,這個商鋪多半就得倒閉,因為沒有人會再跟它打交道,不能賒賬,不能拆借,沒有銀錢往來,任何一家商鋪都活不下 去。反過來,如果行會或者商會不這么干,整個行業就都會受牽連,大家都沒飯吃。
而在張鳴看來,今天,許多食品、藥品的行業協會,之所以不能發揮其本身具有的自凈效應,其原因還是要歸咎于政府監管部門。
張鳴指出:“雖然行業協會是存在的,但只是掛靠行政單位的收費工具,原本就是行業贅疣。所以,食品和藥品的安全,就全靠政府監管部門的監管了。 在此情況下,監管部門一旦出于私利考慮,給予不法企業特殊的綠色通道,允許個別經營者以公關的手段掩蓋其不法行徑,那么帶來的將是整個行業的不法化!”
轉軌期的尷尬
盡管對于食品、藥品的安全問題,多位專家及學者都提出了不同的治理意見,但就其根源,楊建順則認為,出現此現象,是中國社會轉軌期中出現的必然 現象。楊建順向記者介紹了日本的情況,日本戰后經濟蕭條時期,出現過如砒霜奶、水俁病等幾次重大食物中毒事件,隨著后來日本經濟的逐漸好轉,社會誠信機制 逐步建立,圍繞食品安全的種種問題也迎刃而解。
楊建順告訴記者,日本經過上世紀60年代的經濟增長,70年代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社會誠信制度得到了很好的建立和鞏固。現如今,日本的國民對本國的食品更加放心,這一點從日本國內生產食品價格高于進口食品價格既可看出。
而今,中國已取代日本,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楊建順指出,隨著經濟的逐步發展,市場機制的逐步完善,社會的誠信自律機制也必將穩步建立,經營者與行業之間的規范也會隨之加強。
在對于其他學者的采訪中,大多數人對楊建順關于經濟發展帶動食品、藥品安全的說法,也在不同程度上表示了認同,但基于目前問題食品、藥品已經影響到消費者的長遠健康考慮,仍認為有必要在當下采取有力措施,規范食品、藥品市場。
在采訪的最后,沈杰一語道出公眾的心聲:“我們在形容某項偉大的事業時,常說‘功在當代,利在千秋’。而在食品、藥品的安全問題上,卻不要‘功 在個人,貽害千秋’才好。不管目前中國社會處在怎樣的發展時期,吃的東西是否安全都應該是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其有可能對于人體形成長遠危害,萬萬不可 等到千秋之后再行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