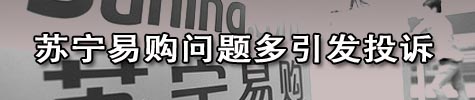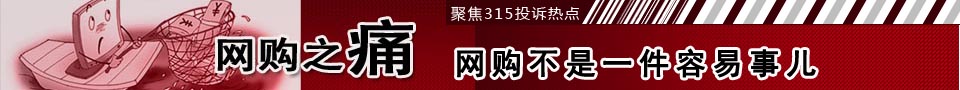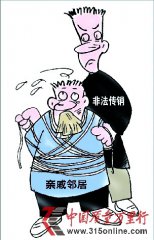廣州從化一家有機農場內,菜農正在采摘蔬菜。馮宙鋒 攝
廣州從化一家有機農場內,菜農正在采摘蔬菜。馮宙鋒 攝
在這食品安全問題層出不窮的時代,一個主婦如何表達她對于健康飲食的渴望呢?
她扔掉了家里所有的果凍和膠囊,拋棄了整盒的茶包和蜜餞,從三年前開始便停止購買牛奶和果汁飲料,走進菜市場,依然要不斷疑心那豆芽是由化肥催長的,茄子打了激素,西紅柿噴了催熟劑,黃瓜買回家還會繼續膨大,通心菜居然沒有蟲眼一定是農藥里泡出來的。
難道就沒有一種辦法,讓主婦們在食品中獲得足夠的安全感嗎?如今,主婦們自發行動起來,并且已經找到一條行之有效的路徑:有機食品。
然而,這同樣是一個魚龍混雜的領域,每一次的選擇和嘗試都考驗著主婦們的辨識力和判斷力。在這個市場的公信力競逐之中,出自官方的“有機認證”體系一次次見證科學手段與商業誠信的毀譽交替,而由民間NGO主導的“社區支持農業”模式則更多地帶著某種理想主義的情結,試圖通過重建生產者與購買者之間基于了解而生的信任,來修復食品安全鏈條。
●南方日報記者 趙新星 李秀婷 實習生 劉振華 江輝
“有機控”主婦
面對各種有機標簽的農產品,一個極端的判斷標準是,越是“歪瓜劣棗”,越值得信賴
凡是請A女士吃飯的人,或多或少都有點壓力,因為她是一個眾所周知的“有機控”。
在食品安全問題愈演愈烈的時代背景之下,A女士對于食品質量的在意簡直達到了“一級戰備”的高度。她家廚房里的蔬菜,全部來自本城的四個小型農場。每逢有NGO或農場舉辦有機農墟,她必定是集市上的購物狂。在任何地方購買任何經過加工的食品,她都要對著配料表嚴格排查添加劑。
懷著對于健康飲食的堅定追求,A女士不厭其煩地接納了有機食品所帶來的種種麻煩。
作為一個三口之家的主婦,A女士得負責通過家庭餐桌消耗掉每周從農場定時配送來的5斤綠葉蔬菜,“一家人吃得臉都綠了”。
除了變著花樣在一頓晚餐里做出5個青菜,每天早上煮湯面下青菜葉,請人上門吃“環保大餐”等等措施之外,每逢工作出差,她還得提前把吃不完的菜送人——實在貴得很,可不能浪費。
朋友組織“團購”北京某農場生產的有機全麥面粉,A女士義不容辭地參加。由于這面粉不含防腐劑,特別容易受潮變質,于是在那一大包面粉寄到后,A女士立即聯合母親又是包餃子又是烙餅又是蒸包子,披星戴月連夜趕工,終于趕在有限的保質期內將所有的有機面粉都做成了有機面食,存入冰箱慢慢吃。
更極端的例子是,她還曾以5塊錢一斤的高價從某個NGO購買其自種自銷的有機大米,結果光是為了清除其中夾雜的谷粒,就硬是讓她的母親戴著老花眼鏡挑了一個晚上。
不過,在品嘗這些自然天成的美味以及踏實的安全感時,A女士會覺得一切都是值得的。現在連她5歲的女兒,都能嘗出有機米飯的獨特味道。“以后每一天都要吃這種米飯。”在吃光一大碗之后,女兒大聲強調:“每一天!”
像A女士一樣,越來越多的主婦們開始采取措施捍衛家庭食品安全,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主婦都能像A女士這樣潛心鉆研有機食品,大多數主婦在面對超市貨架上那些貼著“有機”“綠色”“無公害”等標簽的蔬菜時,都會變成一個猶疑焦慮的選擇困難癥患者。
按照常理推斷,超市里有機蔬菜的龐大供給能力也令人生疑。別說是有機農場,即使是普通的農場也會碰到青黃不接的時候。“沒有貨怎么辦?誰能保證那些號稱‘有機’的農場不是從隔壁農場直接調貨呢?”
社區支持農業
要想吃到放心的雞蛋,那你就去認識那只生蛋的母雞,并親自判斷它是否值得信任吧
既然認證的公信力已經大不如前,那是否意味著它就是可有可無的呢?有機農墟上的攤主們可不一定這么認為。
旅居日本歸來、從事有機農產品貿易多年的農場主楊學彬,在今年3月已經從中綠華夏取得了“有機轉換”認證,但直到今天,他仍然沒有將這一點運用于對外宣傳和營銷之中。
“我們更愿意邀請客戶到農場來參觀,親眼看看我們的菜是怎么種的,種菜的人都是一些什么人,讓他們相信我們。”楊學彬說。
楊學彬的做法,代表了目前廣州地區大多數涉足有機種植的NGO以及個體農場主的共同立場:鼓勵消費者親自參與到農場勞作當中,熟悉生產流程和生產者本身,讓對生產者的信任與對農產品的信任互為基礎——這在公益專業領域當中也就是所說的“社區支持農業”。
上世紀70年代,“社區支持農業”模式在歐美一些國家出現,旨在引導消費者去親自了解農產品的品質、來源及生產方法,從而保障消費者的食品安全;同時生產者也因此獲得相對固定的消費者群體,使農產品的銷量和價格都能保持平穩。這一過程強調的是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直接交流,互惠互信,從而這一模式也被認為超越了冷漠的商業買賣關系,追求在公平貿易的前提下生產優質的農產品,是為“土地正義”。
錢鐘書曾經開過一個著名的玩笑:你吃了一個雞蛋覺得味道不錯,又何必要認識那只生蛋的母雞呢?而“社區支持農業”的邏輯則這樣要求:要想吃到放心的雞蛋,那你就去認識那只生蛋的母雞,并親自判斷它是否值得信任吧。
主婦A女士曾陪同一些外國的專家一起參觀慧靈農場,參觀過程中,翻譯提到“有機”二字,慧靈農場的銷售經理立刻忙不迭地澄清:“我們農場還算不上‘有機’,雖然我們不使用化肥和農藥,但土壤本身離‘有機’標準還有一定差距。農場并不追求搶占市場,初衷也就是為了給服務對象一個通過勞動找回尊嚴的機會。”
在花3分錢就能買到一個有機食品標簽的環境下,這個經理居然主動說明自己的產品沒有達到“有機”要求,這一誠懇的姿態令A女士簡直有些肅然起敬。
A女士非常明白,“仔細想想,農墟上賣的那些東西,沒有任何銷售許可或質量認證,但我們毫不猶豫地購買的原因在于:我了解它們的生產者本人,知道他們有怎樣的價值觀,用的什么原料,經由哪些工序——我信任他們,因為我懂得他們。”
■探訪
生態農場有機轉換期
不能生產銷售“有機產品”
去年9月,廣州有機蔬菜供應商青怡公司被曝以“有機轉換食品”冒充“有機食品”,受到媒體批評。日前,南方日報記者趕往該公司的生態農場探訪。
從廣州出發沿著廣汕公路朝著增城方向行駛至蘿崗區九龍鎮路段附近,拐入一條曲曲折折的泥濘路就可以看見青怡公司的生態農場。
農場約有100余畝,各式的瓜果掛在籬笆上。幾個農民正在菜地里干活,用手在仔細挑選果實。記者看到每個大棚內都有一塊方形的滅蟲板,板上尚有一些剛被粘住不久的蟲子。菜地的四周是一條條淺淺的溝,有機肥溢出的水隨著溝流了出來。附近還有一個規模不大的養雞場。
今年40歲出頭的老楊是該農場新聘的技術工人,但算起來老楊卻有16年的從業經驗。老楊介紹,這個農場里使用的肥料都是有機肥,一包普通的有機肥區區幾百克就高達38元。
有機食品不僅種植成本非常高,而且產出也往往低于預期。老楊說,平均一包種子能收獲4成果實就算是豐收了。“收成并沒有規律,就拿菜心來說,收成好的時候一畝地可以收1000斤,收成不好的時候顆粒無收”。
青怡農場的陳經理介紹,“我們這里雞蛋特別好賣,一箱50個一盒的雞蛋不配送賣80元,常常還來不及供應”。
這一切都顯示著這是一個值得信任的有機農場。但根據嚴格的有機食品的概念,有機與否,還需要通過有關認證機構的認證。據《中國有機產品認證管理辦法》規定,未獲得有機產品認證的產品,不得在產品或者產品包裝及標簽上標注“有機產品”、“有機轉換產品”和“無污染”、“純天然”等文字表述。相關認證產品須文字、圖標、編號、有機產品認證四位一體。
通過公開資料查詢到,2011年5月,青怡農場多種蔬菜通過中綠華夏有機食品認證中心的認證,進入有機食品轉換期生產。但根據相關規定,有機生產經過申請、監察機構檢查完成后,需進入2-3年轉換期,頒發有機轉換證書,在轉換期間生產的產品不能作為有機產品銷售,只能作為有機轉換產品銷售。轉換完成后,頒發有機證書,才算是有機產品。
青怡農場負責人出示的是“有機轉換產品認證證書”。這代表著該農場處于有機轉換期。這即意味著,青怡農場生產的作物還不能稱之為“有機產品”。但記者看到,在產品宣傳冊上,目前仍然有部分商品強調“有機”的身份,比如“有機絲苗米”,以及“有機山茶油”。
記者查詢到,宣傳單上寫的“有機絲苗米”實際包裝卻是該農場品牌絲苗米,商品的簡介有這樣的內容:“依照有機標準進行管理和生產”;有機山茶油則是在包裝上印有“有機轉換”的紅色字樣。
青怡農場表示,由于有機行業正處在萌芽時期,出于擔心“有機轉換”一詞陌生,在部分產品包裝及宣傳冊上強調了“有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