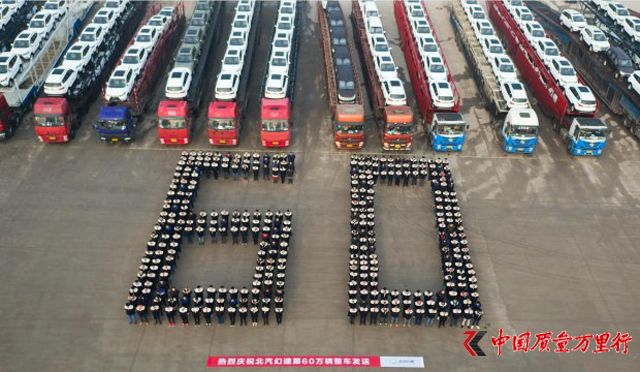近年來,一些新聞熱點事件,常常發生“輿論反轉”現象。事件公布的最后真相,往往與此前引發熱議的說法大相徑庭。
真相還在穿鞋,謠言已行千里。的確,在輿情的流變過程中,有關部門應急措施不當、輿情反饋不力,是導致輿論不斷激化的關鍵原因。若能及時發布權威信息、有針對性地開展輿情引導,一些傳言、謠言就很難有市場。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各種輿論熱點事件形成、發酵和傳播過程中,“標簽化思維”同樣扮演了重要角色。
這種標簽化思維,是人們習慣以“貼標簽”的方式,用長期以來形成的對某個群體、某類事物的刻板印象,評判具體的人、具體的事。在一系列輿論熱點中,許多人在對事實不甚了了的情況下,就草草做出評判,原因在于受非白即黑、以偏概全的標簽化思維所累。
標簽不是輿論的原罪,它是輿論自帶的基因。在日常交往中,人們習慣借助各種標簽,了解和評估某個對象或某種事態。這些標簽包含特定價值和行為判斷,在很大程度上節約了人際交往成本。人們不用為了某個對方不太熟悉的事物多費口舌,只需要用一個彼此熟知的標簽,就能讓對方茅塞頓開。周恩來總理當年率中國政府代表團參加日內瓦會議時,把越劇電影《梁山伯與祝英臺》,介紹成歌劇電影——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一下子就讓外國友人心領神會。這就是巧用標簽的典型事例。
標簽能夠輔助認知,但這并不意味著,凡事都應該進行標簽化認知、標簽化思考,甚至養成一種標簽化思維習慣。同時還應當看到,由于輿論的推波助瀾,標簽化思維正愈益展現出非理性、情緒化的特征,反過來又惡化了輿論生態。
標簽化思維的形成,分為編碼和解碼兩個過程。不難看出,標簽化基本遵循以下編碼路徑:把個案泛化為普遍現象,把偶發總結為必然結果,把特殊描述為一般情況,把細節論定為事物全貌。比如,官員都是腐敗的,城管都是暴力的,路人都是冷漠的,老人都是訛人的……
標簽化思維發揮作用,則是人們對標簽化進行解碼的過程。當一個標簽形成甚至根深蒂固之后,人們就會用這個代表總體印象的標簽,對群體中某個具體個體進行評判。比如,一起普通醫患糾紛,如果當事者是官員身份,輿論關于官員的所有負面印象,就會立刻被調動起來,壓向當事人。事情的本來面貌,反倒鮮有追問。
事實是第一性的,輿論是第二性的。客觀地說,標簽化思維的形成,確有現實基礎。比如輿論場上存在的仇官仇富情結,的確是這個群體中的少數人行為不端、引起公憤形成的。問題在于,個別官員、個別富人的為非作歹,最終卻要所有官員和富人一起買單。無論從認識論角度,還是從社會效果看,都是有害的。
回顧若干起輿論熱點的輿情演變,輿論訴諸慣性思維,在事實尚未調查清楚之前,就匆忙評判的現象并不鮮見。各種謠言之所以能夠滿天飛,恰恰也是因為它們“印證”了標簽化思維形成的刻板印象。在輿論效力越來越大的今天,作為輿論參與者,我們每個人恐怕都得冷靜思考一下,該如何克服標簽化思維,該如何保持冷靜、客觀、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