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多元的社會里,如何阻斷艾滋病的性傳播,不同人盡可各執己見。在不違法不侵犯他人權利的情況下,盡可以各行其是。只是政府系統及有官員或者是準官員、類官員身份的人卻不是什么都可說,都可做的中國正處于轉型之中。我們背負著計劃經濟的遺產,我們不同于發達國家和一般發展中國家有著與政府對應的市民社會。而與艾滋病相關的這一切,正發生在中國的這一時段。
黑龍江的“小姐培訓”、廣東的疾控中心工作人員的扮作嫖客接近小姐,給小姐發安全套,以及有關為防治艾滋病而倡導“百分之百安全套”的爭論,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發生的。
法律和政府政策體現一種國家立場,體現一種主流社會的價值取向。今日的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的法律和政策都是不可能認可性產業的,因為它必須表現出國家和主流社會對自己所倡導的性行為規范的態度。但開放的社會,往往是多元的社會,主流社會所不喜歡的東西難以禁絕,因此,性產業在一定程度上的存在,又是不爭的事實。
由于在結構上同時存在政府管轄法定覆蓋的空間和社會空間,公領域和私領域之間有著清晰的界線,在中國之外的其他國家,可以出現政府不認可性產業,而社會中的一些人、一些非政府組織出于“降低艾滋病所帶來損害”的考慮去幫助性工作者,在無法使她們全部改事他業的情況下,使她們盡可能地在性行為中使用安全套,以減少艾滋病的傳播的現象,但處于轉型中的中國卻很難這樣。
中國從計劃經濟走來,政府意志至今仍顯過強過大,而非政府組織的活動空間卻尚狹小;當社會已趨于多元,本應有一個整體、高效的政府以平衡、協調不同利益、主張時,政府本身竟不一致,不同的部門決策相互矛盾;我們的艾滋病防治策略過多地受到了來自外部別國政府和國際組織“政策開發”的影響,卻較少有國內公眾,特別是利益相關人群的參與;我們的立法和決策缺乏在事先廣泛地聽取不同的意見,及謹慎、周密的論證,缺乏針對本土問題,顯現智慧的自主創新,卻多了許多“技術層面”的簡單模仿。
在性工作者中推行“百分之百安全套”就是這樣。從泰國、柬埔寨等國的經驗,經世界衛生組織等介紹到中國,1999年衛生部在湖北、江蘇、湖南、海南試點,其后,有世界銀行“衛生九貸款項目”和中英項目等又在云南、四川等地推進,到后來中國工、青、婦,以及紅十字會、中國計劃生育協會等的加入,2004年,衛生部等六部委發布《關于預防艾滋病推廣使用安全套(避孕套)的實施意見》,中國疾控中心編制《娛樂場所服務小姐預防艾滋病性病干預工作指南(試用本)》,同年,中央轉移地方補助經費支持全國684個縣(市、區)在娛樂場所開展以推廣使用安全套為主要措施的預防艾滋病工作,2005年,擴展至1327個縣(市、區),但覆蓋人數仍為有限。
整個決策和策略實施都少公眾參與,所以自1999年就由政府衛生主管部門決定做的對性工作者的行為干預,至2006年底仍能于傳媒報道后使輿論大嘩,爭論遽發。非政府組織的缺乏和難以參與,導致只能由政府屬下的、有著準官員身份的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員去做,顯現了同為國家法律的禁娼和為“暗娼”(“娛樂場所服務小姐”)發安全套這兩個具體規定的沖突。作為有準官員身份的人,在明知賣淫違法的情況下不舉報反而發給安全套,不能說不存在角色上的沖突(如果是非政府組織則不是這樣,因為他們并不必須和政府保持絕對的一致)。
以國家財政的錢或者由政府直接接收的國外的錢給違法的賣淫行為提供安全套,于理亦似不當,只對有限的政府試點覆蓋人群發給安全套,致使這種做法的效果于全國性的防治艾滋病的作用有限。準官員對“小姐”只管戴套,不管生存,也使“小姐”很難真正相信他們。至于以準官員身份和“小姐”“同伴”相稱(準官員們在做行為干預時就是這樣和“小姐”相稱的),殊屬不倫。
其實,在一個多元的社會里,阻斷艾滋病的性傳播,是以“禁欲”“忠貞”為當,還是以倡導“百分之百安全套”為當,不同人盡可各執己見;在不違法治原則,不侵犯他人權利的情況下,盡可以各行其是。只是政府系統及有官員或者是準官員、類官員身份的人卻不是什么都可說,都可做的。一些事,政府給民間以空間,支持民間去做即可,直接管得過多,規定得過細,倒麻煩了。另外,不管是對艾滋病還是對其他問題,我們能不能有自己的更適應于本土的創造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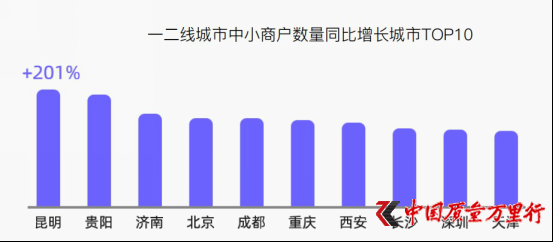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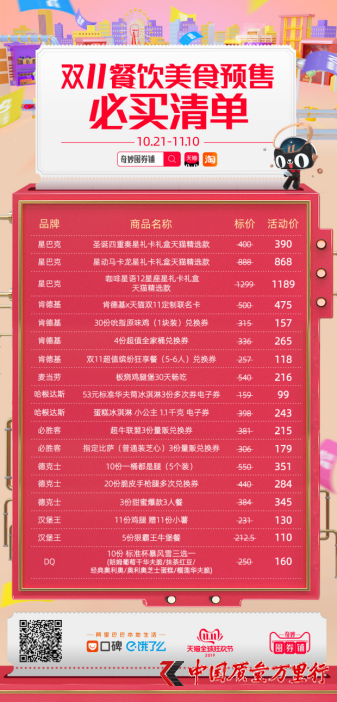




 京公網安備11010502034432號
京公網安備11010502034432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