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消費者的苦惱和焦慮,就是要隨時面對商家的“不守信用”,假、冒、偽、劣太猖獗,而消費者為了不受騙,常常都要通過自學去了解許多領域的所有相關知識。這不是一種“美好的”消費體驗。
消費生活如同“游戲通關”
人們常說“中國市場很復雜”,這種“復雜”一方面是指市場容量極大,不同層級或不同生態的現象都存在,但另一方面則是指其中的信息干擾度很大,運作不透明,栽進去會吃大虧——這大抵就像我們涉世未深時父母告誡說“外面社會很復雜”一樣,意指陌生人的環境中無法像對家人那樣建立信任關系。
這樣一種現實的存在,就迫使中國人要耗費大量精力去篩選、排除掉那些干擾信息,才能找到自己想要的事物——夸張一點說,這有時就像是一個通關游戲,你得先游過橫亙在你和目標之間的鱷魚池,打敗那些怪獸,才能得償所愿。
這倒也并不是說你遇到的信息都是假的,或者說那些廣告和中介都是騙人的,而是說,大部分普通消費者其實根本無力去判斷真假,即便他們已經相當努力去識別了。雖然經濟學上有所謂“理性人”的假定,但事實上每一普通的消費者的理性都是有限的:一個日常生活中事事精明的婦女,連青菜漲價一毛錢都瞞不過她,但她卻可能輕易上當去買一件假棉絲被或某個收益率很高但風險極大的理財產品,因為關于這些產品的常識,超出了她能根據自己生活經驗判斷的范圍。
“從眾心理”與“迷信權威”
有一次,路過一個停車場,看到檔桿上的廣告寫著“3000萬人都在用”,忍不住發笑,覺得這真是中國人從眾心理的寫照,連停車的檔桿也要強調有多少人在使用;不過轉念一想,這其實也是人們對特殊環境的正常反應。那些諸如“大平臺,更放心”、“2億中國人都在用”之類吹噓自身實力的廣告之所以大行其道,與其說是利用中國人的“從眾心理”,倒不如說是在順應人們的一種心理渴求:在市場干擾度很大的時候,如何用簡便的方法找出值得自己信賴的。
此時“權威”就成了一種方便的篩選信號,因為那么多人都在選,應該沒錯,就像看到路邊排長隊,甚至還不知道是賣什么,自己也排上去。這固然也有“從眾”的成分,但從根本上說卻不是沒有思考,恰恰是因為這種“搭便車”的方法常常可以幫助人們不用費神卻能少受騙。
有一年我去山東做下鄉調查,在曹縣的一個小店里,發現店主在看中央臺的天氣預報,我問他為何不換到山東臺,畢竟中央臺僅提到山東寥寥幾個城市的天氣,甚至不包括菏澤當地。他想也不想就說:“因為中央臺的天氣預報更準。”
在現實中,我們還常能看到另一種情形:很多人就算是感冒發燒這樣的小病也要去大醫院就診。如果說這種心態是“迷信權威”,那這背后的原因可能在于:人們缺乏可靠的信息來判斷,又沒可資憑信的第三方機構提供信用評級(就算有,他也不信其客觀中立性,因為中國社會中的現實是,如果信用很重要,那就會有人設法去鉆營作假),在這種情況下,人們自然認為,最簡便可信的信號就是那些“權威機構”。
相信大公司大品牌十多年前在一次職場培訓中,一位美國教授說,商業提案技巧中首要的一點,是不要對客戶展現傲慢——一上來就說自家是“國際大公司”,客戶會覺得“那又怎樣?這跟我有什么關系?”他強調,這是尊重客戶,應把重點放在“我能為你提供什么專業服務”上。
話是這么說,在現實中卻不難發現,在國內市場上“大公司”
的頭銜加持就如同溢價20%(甚至更高),因為它可以免除人們的許多擔憂:
1)至少很多人做過選擇,你的風險就減輕了;2)大公司的操作通常是規范的,不會胡來;3)它不會隨時倒掉或跑路;4)當然,如果它同時還低價,那就更好了。
這樣說起來,中國人的消費心理其實低得可憐,它要的只是一種基本的保障。為何很多廣告中都強調“買了放心”?這正說明,老百姓在意的不僅是商品/服務的品質,還擔心買到假貨或受騙。所謂“放心”、“大公司”、“大品牌”之類的說辭,都是針對這樣在市場信用匱乏情況下的一種避險心理——附帶說一句,很多人喜歡讀經典書籍,往往也是類似心態,因為評論不發達,他也不清楚哪些書好,那么可取之道簡明快捷的辦法,就是去讀那些已經被證明為可靠的“經典”。
由于人們在作出選擇時并不單純只是商品/服務本身,還需要其它復雜的信息來供判斷商品或服務的優劣,因而順理成章的一點便是:中國的廣告也往往并不只單純聚焦于自身的品質。
福建的惠泉啤酒一度在中央臺大打廣告,這乍看違背廣告原理,因為惠泉當時覆蓋的福建、江西兩省僅占全國1/20的人口,這意味著大部分人即便看到廣告也無法購買其產品。當我和當時負責投放其廣告的同學聊起時,他笑說:“這你就不懂了。客戶可是非常高興,因為不少人和他們老板說:你們現在很有實力啊,廣告都上中央臺了!”
中國的消費者在買車、洋酒、奢侈品時常常特別在意產品的社會聲望價值,現實也一再證明,很多經銷商會把這看作是企業實力的表現,以至于某些品牌一段時間不上中央臺,就會被緊張地問及,是不是現金流出現了問題。
借用進化論的術語,這就像是某種“昂貴信號”。達爾文曾提出“性選擇”(sexualselection)學說解釋大部分雄性動物為何會進化出一些對生存影響不大的第二性征,例如雄孔雀巨大的尾羽雖然很美,但其實冗余無用;他認為,這是因為這些會給雌性一個信號:“你看我,只有像我這樣強壯的雄性,才能負擔得起這樣一個累贅而仍然不礙事。”企業為此迎合消費者這種心理篩選,因為對于琳瑯滿目的市場和相對盲目的消費者來說,在某種程度上秉持類似的心理預期,是希望通過一些可見的值得信任的信息來避開消費風險。
然而人們也很清楚,正是由于這些信號很容易取信于人,因而也常常成為操縱的對象。《我不是藥神》里販賣假藥的張長林便冒充院士來推銷其毫無療效的假藥,因為“院士”頭銜看上去相當可信。
除了冒充之外,很多真的專家也確實因各種原因(或利益收買、或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利用)變成了共謀,更何況“專家”本身有時也不完全是客觀評定出來的,一個科研單位里誰先評上職稱,往往未必純是水平,有時還可能是“他已經等了很多年了”甚至“照顧下他家里困難”。加上一些專家的發言有時與民眾的認知反差巨大,反倒使中國社會出現了一種對專家不信任的心理。
急需建立更多“第三方信用”
漢語詞典中所謂“信用”,是指依附在人之間、單位之間和商品交易之間形成的一種相互信任的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而信譽構成了人之間、單位之間、商品交易之間的雙方自覺自愿的反復交往,消費者甚至愿意付出更多的錢來延續這種關系。言不信者,行不果。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信用是整個社會運轉的基礎,沒有信用,社會和市場必將陷于混亂。作為一種基礎性公共服務,每個國家都建有自己的信用體系。
關于信用體系的建立問題,從2003年“十六大”時就已經開始商討這個問題,十五年過去了。
以“信用體系”為關鍵字,從中央政府網站搜索可以看到,中國的信用體系建設一直沒有間斷,包括各部門自有的信用體系信息庫:
公安部公民身份系統,公安部全國公民身份證號碼查詢服務中心;全國組織機構代碼管理中心——誠信體系實名制公開查詢;中國人民銀行征信中心,通過這一信用平臺,個人可以坐在家里查詢各種個人信用信息,打印個人信用報告。這一舉措被認為能夠推動整個社會誠信體系建設,尤其是小微企業,將與個人信用記錄捆綁;教育部學歷認證系統:學歷認證——中國高等教育學生信息網(學信網);住建部:全國建筑市場誠信信息平臺;(原)國家質檢總局產品質量信用記錄;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全國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等等。
作為以國家和政府信譽做擔保的各部門信用平臺,在維護社會穩定和公平的過程,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與此同時,我國市場化的信用體系建設也在建立和完善,“支付寶”就是中國特色市場經濟的一個創舉,它從規則制度和技術保障層面解決了人們特別是消費者與商家的相互信任問題。
因此,我們需要更多類似這樣的“第三方信用”。
不過很顯然,我國這種市場化的“第三方信用”平臺還遠遠不夠。在“信用”已成為稀缺資源的當下,其實這也蘊藏著無限商機;如果建立更多公益性的這種信用平臺,那才真是消費者的福音。





![[器度] 將亮相第42屆中國(上海)國際家具博覽會](http://www.zu001.cn/uploadfile/2018/0910/20180910045808352.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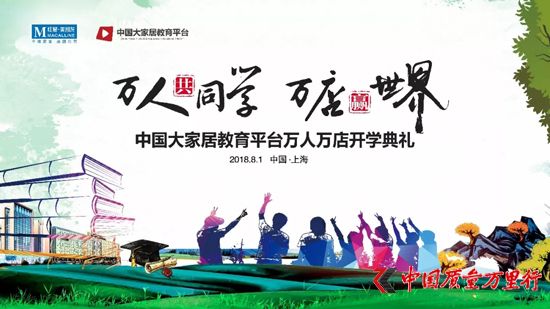


 京公網安備11010502034432號
京公網安備11010502034432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