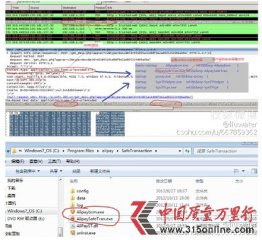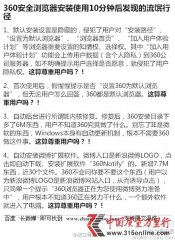與“十五”末相比,2010年版權輸出總量增長275%,版權引進與版權輸出之比從7.2∶1縮小至2.9∶1左右
美國人艾瑞克很忙。
他一邊準備向國外出版社推介描寫中國城市化的文學作品以及中青年作家,一邊給中外出版集團的收購、并購提供完備的市場調研報告。
艾瑞克所從事的是中國文學作品翻譯以及代理。他已經“入行”11年了。
艾瑞克不愿意用“漢學家”來形容自己,覺得帽子太大。一位“代理人”向國際出版市場推銷四五位作家與“漢學家”的稱呼確實并不相稱,但目前能夠“走出去”的當代作家也只不過20多位。
隨著中國作家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國外將對現代化的中國越來越好奇。這是艾瑞克的直覺判斷。
當然,也有幾位漢學家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認為,莫言獲獎暫時改變不了目前中國出版貿易的格局。
艱難的“走出去”
走上專業中國文學翻譯與出版顧問之路,艾瑞克說完全出于對漢語及文學的沖動性熱愛,并非理性規劃。
艾瑞克談起其喜歡的中國作家,王朔、劉震云等都在其中。其嘗試翻譯的第一部作品是王小波的雜文散文全集《沉默的大多數》,發表的第一部翻譯作品是2006年在香港英文版的文學雜志上王小波的《我的精神家園》。
從2005年開始,艾瑞克將自己認為不錯的中國作家以及作品介紹給美英出版社以及文學雜志社。
從這一年開始,“中國出版走出去工程”開始實施,包括中國出版集團、中國國際出版傳媒集團(外文局)在內的出版集團,開始通過獨資、合資、合作等方式,在境外辦刊、辦報、辦社、辦廠、辦店。
“很難真正落地生根,有些海外分公司、出版分社在最初成立時雄心勃勃,計劃每年10個品種,但實際運行下來只能完成2~3個品種,而且印量普遍在800~2000冊之間。當時,相當部分的海外機構還停留在收集信息等服務層面,絕大部分還沒有開展出版業務。”一家出版集團的負責人告訴本報記者。
實際上,這些基本是以“版權銷售”為核心,國內出版集團免除了翻譯成本,但國外一家出版社要破解銷售市場的難題。
“很多時候,國外的出版社與文學雜志社并不知道我們介紹的中國作家是誰,更不要說作品,也不知道中國文學的流派有哪些。因此,美國的出版商雖然對中國作品很感興趣,但真正談成功并不容易。”艾瑞克表示。
如此大背景下,通過譯者向出版社推薦引入的做法,成為沿用至今“走出去”的主要方式之一。
作為代理人之一的艾瑞克,能夠做的是一本一本書、一個一個人推介。
“至今,‘走出去’的中國作家沒有一本書在國際上成為暢銷圖書。”一位代理人告訴本報記者。
難以為繼的代理費
面對壓力,中國圖書出版界采取了一些積極措施。其中最為重要的一條措施,就是“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的實施,通過資助翻譯費用鼓勵外國出版機構翻譯出版中國圖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