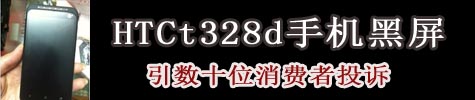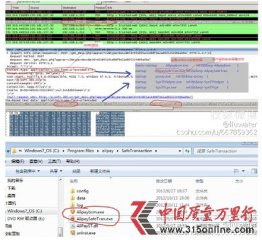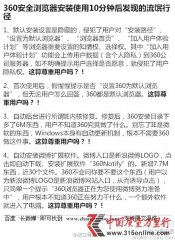LED與光伏行業泡沫的破滅昭示需開辟新發展路徑
不能說所有企業都要有自主知識產權,但也不能全部是低層次的企業。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需要多個產業環節,多種產業形態,不可能都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代工也沒問題,應允許不同技術層次的企業存在。但是,如果普遍是低層次、低水平企業,對整個產業的發展一定是硬傷。
——— 深圳大學中國經濟特區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易明
深圳高交會近年已成為新興產業展示的舞臺。尤其是今年,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與節能環保、生物、高端裝備制造、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車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自主創新成果得到集中展示。新興產業熱度空前,引領產業發展、高科技發展的方向。但是,狂熱背后需要冷思考。各地不約而同上馬新興產業已經顯出“一窩蜂”的狀態,而深圳上馬的六大戰略性新興產業是否都足夠“戰略性”?反觀企業,LE D、光伏泡沫的破滅,一定程度上已經昭示:沒有核心技術、關鍵技術的支持,新興產業發展仍將走上一條低水平的道路。新興產業,呼嘯而來,能執牛耳否?
LE D幻滅光伏行業凄慘
深圳布吉上雪科技城的愿景光工業園,已經失去往日喧囂。這里的“主人”曾是國內LED行業五強之一。該公司成立于2005年,第二年銷售總額突破千萬,之后兩年銷售額如火箭發射,達到2.6億元。
過去幾年,愿景光的崛起代表LED行業的普遍現象,而它的衰落,同樣具有普遍意義。今年6月29日,愿景光突然宣告破產,年初起開始拖欠工人工資,拖欠廠房裝修方工程款,欠銀行貸款也高達上千萬元。由于LED行業之前相繼有多家知名企業倒閉破產,愿景光的破產消息已經不具爆炸性,但還是讓整個行業的悲情氣氛更加濃厚。
回望愿景光的浮沉,固然有全球經濟下滑大環境影響,但也是LE D這個被譽為新興產業、朝陽工業核心技術缺乏、發展層次低下的必然。近年,全國不少地方政府大力推廣LED項目,整個行業過了幾年好日子。但由于LED企業多數缺乏對核心技術的掌握,使得LED企業基本集中在低端市場,基本靠打價格戰,逐漸走入惡性競爭的循環,最終難以為繼。
與LED境遇類似甚至更凄慘的是光伏行業。數據顯示,目前國內光伏行業利潤率已從2007年的139%下滑到20%。在500多家光伏企業中,1/3中小企業產能利用率在20%-30%,基本處于停產或半停產狀態。
也許LED、光伏產業表現得過于極端,但對于新興產業而言,在各地扶持政策呼嘯而出的背景下,在大量企業一哄而上的環境下,產能過剩、同質化競爭、低水平增長等,是不得不思考的現實問題。
新興產業發展大躍進?
在發展新興產業方面,深圳早在2008年,在全國較早規劃戰略性新興產業,2009年起先后編制出臺生物、互聯網、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術和文化創意等六大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振興發展規劃及配套政策。到2015年,深圳戰略性新興產業規模將超2萬億元。
如今,全國各地隨處可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字眼,仿佛哪個地方沒提出發展新興產業的目標,誰就落伍。有專家統計,除西藏外,全國各省市幾乎把新能源及相關產業列為戰略性新興產業。學界多次呼吁發展新興產業要避免再次出現“大躍進”。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曾提醒說,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出現一些苗頭,應該引起注意。比如,一哄而起的從眾化,一些政府機構指定技術發展的路線,指定發展的產業門類,甚至直接確定投資等。
最新數據顯示,一哄而上的新興產業,在短暫高增長之后面臨成長困境。截至10月29日,根據超過400家具有新興產業背景的上市公司發布的前三季度業績,新興產業公司整體凈利潤同比下滑13.1%,遠超過其他上市公司的業績降幅。深圳的數據并沒有反映出下滑態勢,生物、互聯網、新能源三大戰略性新興產業產值增長38.1%,增速高于GDP增速2倍以上。
“從統計指標來看,增長速度非常快,也涌現一批相當有影響的企業。”深圳大學中國經濟特區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易明說,與內地很多省市相比,深圳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時機已經成熟,條件具備,因此相對富有成效,“政府要有所為,需要適度超前,但不能過度超前,否則就有拔苗助長的嫌疑”。
在袁易明看來,深圳由于土地空間等限制,靠原來的產業已無法實現新的發展目標,必須要找尋新的東西。深圳擁有一批高科技人才,比鄰香港也使其對國際產業信息反應敏感,使其比內地很多城市更迫切需要發展新興產業。
即便深圳具備發展新興產業的時機與條件,袁易明仍認為政府在新興產業政策上應非常慎重,“政府政策一方面會是真金白銀,看得見的好處,一方面會引導企業產生‘搭便車’的心態,形成產業發展的羊群效應。企業在這個過程中沒法做更多評估,如果政府判斷不準確,企業盲目跟從,最后就是產能過剩,LED、光伏就是典型”。
低層次低水平發展路徑
比產能過剩更讓人擔心的是,新興產業發展有走上老路嫌疑,大量企業在復制著傳統產業低層次、低水平發展的路徑。
LED行業的衰落足以說明在核心技術欠缺情況下,低水平競爭帶來的惡果。曾經有媒體報道,國內很多光伏企業飽受核心技術缺乏之苦,硅料提純采用德國技術,硅片生產多晶爐采用美國設備,生產硅片電池七道工藝,五道需要進口設備等。
新興產業贏利模式幾乎與之前大量“中國制造”如出一轍。有專家指出,沒有核心技術,新材料、生物技術和新醫藥、節能環保等新興產業可能像過去信息產業一樣,身為高端產業卻不能制造芯片,只能生產鼠標、鍵盤、外殼等低端產品,淪為新興產業加工制造業。
以智能手機為主業的深圳酷派公司,近年在全球通信行業的激烈競爭環境中倍感壓力,主業難以抬頭,只能在土地運作另辟蹊徑,以該公司為主體的母公司中國無線,2011年凈利潤為2.71億港元,但“其他收入及盈利”達3.2億港元,比上年增加近50%。這意味著,如果刨除此部分收益,主業凈利潤為負值。以智能手機為主業的公司,卻主要依靠各地土地重估增值及租金收入維持財報的盈利。
在新興產業領域,缺乏關鍵技術、主業難以為繼已成為共性問題,因此新興產業“圈地”現象也明顯。業內普遍認為,新興產業“有高端之名卻行低端之實”,走上代工企業老路的問題,已經到了不得不直面的時刻。
“不能說所有企業都要有自主知識產權,但也不能全部是低層次的企業。”袁易明說,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需要多個產業環節,多種產業形態,不可能都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代工也沒問題,應允許不同技術層次的企業存在。但是,如果普遍是低層次、低水平企業,對整個產業的發展一定是硬傷。
政府千萬別越俎代庖
從最早出臺三大戰略性新興產業扶持政策至今,深圳謀劃新興產業已經近五年。袁易明表示,眼下,對深圳新興產業系列政策進行科學評估,已經是時候,“過去做得怎么樣,未來應當怎樣,需要中期評估,需要新政策。”
袁易明說,如何引導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是一門藝術,但政府是否把握得好,是不是形成以市場為主體,還有待檢驗,“一味跟風不是好政策。”深圳新興產業系列政策細度不夠,應當做得更細,“產業政策不能一刀切,對不同產業,同一產業不同環節等,都要有針對性政策,這樣才有針對性,才可以引導產業去發展”。
在產業選擇上,袁易明說不能采取撒胡椒面的做法,要區別對待,“比如生物產業,如果要產業化,需要很強大的技術、人才儲備,對研究開發要求非常高,如果分配的資源與其他行業一樣,會導致部分資源配置效率低”。
而在發展新興產業時,不要緊盯大企業,重要的是關注中等規模企業,因為大企業拿到資源的能力較強,中小企業則需要更多的培育。“政府要做的是以產業為切入點,不是扶持某個具體的企業。”袁易明表示,政府可以承擔一些共性技術、關鍵技術的研發,可以首先應用、示范,啟動市場,以進一步拉動全社會的消費,不該政府做的,千萬不要越俎代庖。
記者觀察
高交會價值在哪里
北風吹,鑼鼓響,又是一年高交會。趕集一樣的人群涌向深圳會展中心。展館外的大嬸阿姨們依然在熱情兜售黃牛票,場館里的年輕女孩們仍然用低胸和熱舞吸引市民。從表現手法與受普通市民歡迎程度而言,深圳高交會不亞于性博覽會。雖然會展中心入口要爬上一層又一層的高高臺階,但進入其中的高交會參展項目并非個個高精尖。
有這個城市最為熟知的山寨電子產品;有各種方便生活的小發明如鍋碗瓢盆;甚至曾有擺攤賣手鏈鐲子的……這些產品,無論如何也算不上高科技產品。但是,它們硬生生擠進了高交會會場,也吸引不少人看熱鬧。
很多第一次參觀高交會的人未免驚訝,高交會原來與生活這么貼近。貼近生活是好事,但在滿天飛的傳單、嘈雜吆喝聲中,往往容易使人忘記身處“中國科技第一展”。這個號稱中國規模最大、最具影響力的科技類展會,13年前首屆開始,深圳就雄心勃勃地定目標為以高交會為平臺,為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提供支持與服務,探索“高交會—技術產權產易—創業板市場”一條龍科技創業新模式等。
那時候,也是深圳喊出打造高科技新興產業的口號不久。10多年過去了,深圳一批企業崛起,如中興華為已經成為深圳高新技術企業代表。深圳給了“華為中興”們最好的成長環境,讓它們專注科技實業,在群狼逐鹿的國際市場走出一條持續升級之路。然而,這個城市尚未擺脫創新乏力的宿命,整個社會距離創新機制、創新氛圍依然很遠。
為了短期利益,諸多企業淪為沒有任何技術含量的拙劣模仿者。這些年,也是深圳山寨產品從炙手可熱到岌岌可危的時光。
沒有自己的核心競爭力,只能一味在低端產業上吊死。
同樣,沒有更高的高科技,高交會容易變味。“高交會原本有很強的專業性,但現在成了一個大市場。”深圳市人大常委會委員王富海評價說。高交會的意義并不在于人來人往,鑼鼓喧天很熱鬧,也不在于提供好玩新奇的小發明。對于致力打造國家創新型城市的深圳而言,高交會實際上承擔非常重要的使命。如果它能對城市創新氛圍的培育、對產業轉型升級的促進起到一定作用,這才是真正的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