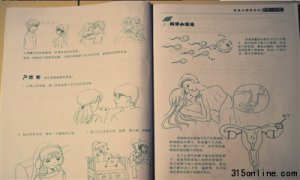而讓他感到遺憾的是,“恰恰到了最關鍵的地方‘本工作的目的與研究內容’這一部分寫得很不靠譜兒,或者是寫不到點子上。”
華中科技大學電氣與電子工程學院在讀博士生馮登參加過多次師兄師姐的博士論文答辯,對一些“核心內容不多,很多文字沒有意義,堆砌制作的論文”深為反感,“很多人的博士學位論文‘頭重腳輕’,前面引用了很多國內外文獻,可后面自己所做的工作卻不多。”
“論文的厚度并不能決定其質量。”中山大學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博士生導師明確表示,純屬為了達到要求而湊字數,有時還會適得其反。大量引用參考文獻,論文離自己的中心論題反而會越來越遠。
高伯龍院士翻閱一些大師的名著,更是驚訝地發現:文章一般不長,參考文獻很少,比如愛因斯坦在相對論中提出質能關系式的德文文章共3頁,1篇參考文獻;沃森·克里克提出DNA雙螺旋結構的英文文章約1頁,“這兩篇文章,被公認為是劃時代的著作。”
“全國高等學校都要向國際一流進軍。是否應該向他們學習呢?我們的博士學位論文能否壓縮到50頁左右呢?”高伯龍提出疑問。
別敦榮教授則不贊同簡單地用期刊論文或學術界一些經典論文的篇幅來要求博士學位論文。
“博士學位論文要有一定的厚度,這是博士學位論文的性質所決定的。” 別敦榮教授認為,博士學位論文不應當只是學術觀點的闡述,還有其他要求,比如,關于博士學位論文選題的論證、關于相關科學文獻的綜述、對研究過程的介紹等,“這都是學位論文所特有的,要完成這些工作任務,就需要有一定的篇幅。”
但他同樣認為,針對不同學科特點,博士畢業論文的厚度依然需要一個大致的量化標準。
在博士學位論文的篇幅越來越長的同時,博士生創新能力不足的問題正廣受詬病。
多個部委聯合組織的一份針對中國博士生質量的大規模調查顯示,博士生導師認為博士生創新能力“較高”、“一般”和“較低”的比例分別為29.7%、62.7%和7.6%。有專家指出,原始創新不足是我國博士論文與世界一流大學博士論文的最大差距。
高校開始發出積極信號
論文要求逐漸由“字數”向“創新點”傾斜
畢業于武漢大學信息安全專業的王后珍博士還記得當年交學位論文初稿時的情景,與周圍的同學相比,自己的論文顯得有些“寒磣”:很多同學的博士畢業論文大多厚如磚頭,自己只有70余頁的論文在裝訂時卻連側面上的標題都印不上去。
與同學交流后才知道,很多同學認為“只有寫厚了,才會覺得踏實”,班里最厚的一本論文甚至達到200多頁。
出人意料的是,論文答辯結束時,王后珍薄薄的論文因為思路清晰、有創新點在眾“磚塊”中脫穎而出,“意外地”獲得了為數不多的“優秀”。
高校里已經開始發出積極的信號。
華中科技大學電氣與電子工程學院博士生馮登雖然離畢業還有兩年,但導師已經要求他開始考慮自己的博士學位論文了,“從論文大綱到最終定稿都要有明確的規劃”。
面對學位論文的要求,馮登壓力很大,但這份壓力并非來自字數,而是論文核心內容的創新點——導師明確提出:“論文一定要有創新點,有自己的想法,在科研上有所突破才是最重要的。”
吳庸博士還記得一個當年在校時同學間私下總結的“潛規則”:畢業論文首先就是要把字數湊夠了,評審專家們肯定都得互相給面子,但表面看上去還要說得過去,“再說,一些飛來飛去的‘老板’也不一定有時間認真去讀內容。”
而現在,他留心觀察發現對博士學位論文質量的要求正不斷提高,高校對論文的字數要求有所寬松,漸漸把重心落實到博士生在讀期間具體的研究內容和其所做的實際工作上來了。
吳庸說,盲評(學位論文評審的一種制度)的比例加大了,突襲式的抽查更是讓人心驚肉跳,各方對畢業論文創新的追求自然也多起來。
華中科技大學的馬洪教授說,自己在評閱博士學位論文時,判斷的主要標準一般是“看其研究工作有沒有價值,論文本身所研究的核心內容是不是值得研究的問題,博士生本身做了多少工作”,而非依據論文的厚薄下定論。
每年博士生交學位論文初稿時,他常常對還在讀的博士們明確態度:“希望論文能夠精簡一些以減輕博導們的審閱壓力。”
武大數學系黃崇超教授介紹,在國外,本專業的論文經常要請其他專業的人士來做評價,看看非本專業人士對論文內容能不能做到有大致的了解,以驗證論文的可讀性,“所以說,論文頁數的多少不應該成為博士學位論文的評價標準,論文的厚薄也說明不了什么。”
他表示,自己欣賞的還是那種“自己做的東西,論文中有足夠創新點”的論文。
記者 雷宇 實習生 范紅玉 夏夢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