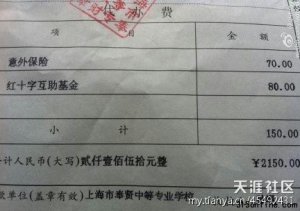教育需求多樣化催生“在家上學”
讓眾多在家上學或者互助上學的家長聚到大理的,歸功于一位叫徐雪金的浙江人。他在義烏創辦了“在家上學聯盟”的網站,網站上不僅有各類教育信息,還有以城市為單位的分論壇。
徐雪金在論壇中這樣自我介紹:“我,一婦男,帶兩個自己的孩子和外甥在家上學。大女兒7歲,不上小學;小兒子2.5歲,不上幼兒園;外甥3.4歲,不上幼兒園。”
“在家上學”研討會最小的一位參與者是剛剛年滿12歲的袁小逸。她一個人從義烏坐汽車到杭州,坐飛機到昆明,然后轉乘大巴車坐了4個小時到達大理。
“我也到學校上過一兩個學期,后來不愿去了,學得太慢。”袁小逸在父親的指導下,不僅已經學完了初中課程,還寫了自傳《私塾女孩袁小逸》。她還是一名小先生,從4歲起就教同齡小孩,如今在父親創辦的學堂和網上課堂教英語。
網絡時代應重新審視家庭的教育功能
有意思的是,選擇在家上學的實踐者中,男性占了大多數。
“這次前來聚會的‘在家上學’踐行者,以爸爸居多,讓我看到了男性力量的睿智、大氣、承擔與使命感!”葉萬紅感慨,她的老公也已辭職參與學堂建設。確實,在家上學公認的幾位“領袖式”人物,都是父親。
在21世紀教育研究院的研究人員看來,父親更多參與孩子教育是網絡時代的一個新信號。在工業化社會以前,下一代的教育主要由家庭完成。工業時代的社會分工細化,學校教育一支獨大,傳統的家庭教育逐漸衰弱甚至被忽視。進入網絡時代,生活及社會交往方式發生變化,信息和知識的傳播、獲取方式也發生了重大改變。于是,家庭教育的功能被重新正視。
王曉峰的觀點是,工業社會之前,教育是進行全人教育,而到了工業社會,由于學校的興起,教育就變成了技能教育,學校的功能也只是知識傳承。
“目前,我國‘在家上學’的實踐在教育理念、內容、方法上呈現多元,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就是重視家庭教育的價值,重視家長的直接參與,強調對兒童的愛和尊重,實施以每一個學生為本的個性化的教育。”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楊東平說,“這一實踐順應了社會結構分化、教育需求多樣化的發展趨勢,對于增加教育的選擇性、豐富性和提供高品質的教學,滿足不同群體的教育需求具有重要價值。”
120萬名美國兒童在家上學
在國際上,“在家上學”有一個通用英文詞“homeschooling”,是美國19世紀末開始萌芽的一種獨特的教育方式,并于20世紀50年代蓬勃發展。當時,社會上一些擁有較好經濟實力和較高文化素質的中產階級家庭,由于認清了學校教育的程序化、機械化等弊端,同時出于宗教、安全等方面的考慮,不愿再將孩子送入學校,從而選擇了自己在家教育孩子的方式。他們自己帶領孩子學習,更加關注孩子的個性、天賦和興趣點,在此基礎上選擇適當的教育方法和學習重點。
20世紀70年代以前,在美國大多數州,“在家上學”被認為是一件違法的事情,一直受到公共管理機構的“圍剿”。很多家長為了實施在家上學方案,唯一的辦法就是東躲西藏。經過多方努力,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各州陸續出臺相關法律,確認在家上學的合法地位,并出臺相應支撐體系。1993年秋季,“在家上學”最終在美國50個州實現合法化。“在家上學”的孩子雖然拿不到正規學校的文憑,但可以憑借全美大學入學考試SAT(相當于中國的高考)的成績獲得大多數高等學校的承認。
在美國,各種各樣的調查統計顯示,在家上學兒童比例增長很快。1985年,僅有5萬名在家上學兒童;到1992年,則有30萬名在家上學兒童;1999年,美國教育部估計數量已經達到85萬人。美國駐華使館中文資料顯示,2004年有多達120萬名美國兒童在家里接受教育,在家上學已經成為美國增長速度最快的一種教育形式。
王玉國是北京師范大學的在讀博士生,他的研究發現,美國之所以出現越來越多在家上學的學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學習效果明顯。一項研究表明,在美國范圍內的標準化學術成就測試中,在家庭學校讀書的學生成績勝過公辦學校的學生,并且各學科的分數差異都在30~37個百分點。
現今“在家上學”的家庭教育理念及其實踐已經作為一種教育自由選擇運動被推廣到許多國家和地區,如加拿大、英國、泰國以及我國臺灣及香港地區。 (本報記者 李新玲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