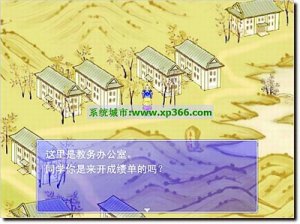初中畢業進入職校,入學第6天即從學校所在地貴州貴陽遠赴廣東東莞“頂崗實習”,在一家電子廠流水線上一干就是7個月。第一個月拿了100元,第二三個月各150元,第四個月200元,第五個月180元,第六個月330元,最后一個月200元——7個月總共收入1310元。
小余說,每月的“工資”都由學校發放,“學校說是‘零花錢’”,而那段時間她每天在工廠工作11~13個小時,雙休日還經常加班。
這樣的“頂崗實習”,幾乎占據了她3年學習生涯的大半。那段時間,她自稱“學生工”,第一次被學校組織去打工時她年僅17歲。一周前,她和其他68名“學生工”一起委托律師,為那段“不明不白”的3年時光“討公道”。
69名維權學生大多出生于1990年至1993年之間,許多人第一次外出“實習”時未滿18周歲,個別人甚至未滿16周歲。
實習工資用來交學費
2007年5月,初中畢業的小余堅定地告訴母親,自己“一定要到‘貴陽市國防學校’讀書,因為招生老師穿的是軍裝,而且到那兒上學不用交學費”。
小余家庭困難,父母均在家務農,母親身體還不好。小余以為,自己念了所“好學校”,將來學了本領就能出去打工掙錢。
現實是,她2007年5月21日入學,27日就突然有了去東莞“打工掙錢”的機會,只不過,這趟遠行“實習”掙的是“學費”。3個學年中,除去寒暑假,小余有15個月在打工“交學費”。
她說自己從未見過工資條,也從未直接從企業拿過一分錢,所有“工資”都是學校以“零花錢”名義發的。她判斷,企業直接將工資打給學校,“工廠發了多少不知道,學校扣了多少也不知道”。
為此,中國青年報記者專門致電東莞一家接受該校學生“實習”的企業的人事處,對方拒絕就此做出解釋。
在一封由69名維權學生寫給貴陽市物價局的投訴信內,他們詳細羅列了3年來在職校學習繳納的費用:包括入學保證金850元、學雜費9300元、裝備費1200元、生活費5410元、保險180元、體檢費50元、班費200元、外聯費800元、實習車費756元、辦證費756元,共計19502元。
按照入學前學校與學生的約定,上述費用將從他們日后“頂崗實習”所得中扣除,850元保證金將在學生畢業后退還。
名目眾多的收費條目令學生摸不著頭腦。根據《中等職業學校收費管理暫行辦法》第12條規定,中等職業學校除收取學費和住宿費以外,未經財政部等部門聯合批準或省級人民政府批準,不得再向學生收取任何費用。且收取學費應使用“省級財政部門統一印制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專用票據”。
小余告訴記者,學校發的“學費明細單”顯示,第一年學費為7000余元,第二三年分別為5000余元。她告訴記者,所有與她一起維權的“學生工”均未收到正規發票,畢業后也沒有拿到850元保證金,“只有學費明細和收據,850元說是用來抵學費了”。
維權學生代表曾于今年5月3日赴貴陽市物價局收費處查詢物價部門核準的學校收費標準,結果查無“貴陽市國防學校”記錄,小余說:“只有2008年‘貴州省國防軍事學校’的收費標準為1200元(其中包括900元學費和300元住宿費),2010年‘長征職業學校’的收費標準為1000元。”
對此,貴陽市國防學校副校長周天華(小余等人就讀學校實為“貴陽市國防學校北院,亦稱貴陽長征職業學校”,由周天華主持工作——記者注)回應,學校學費由物價部門核準為每學年2000元,學校實際收取1600元。
國家助學金用于“生活費開支”?
那么,“天價”學費之下,教學質量能否得到充分保證呢?
除小余外,另有小羅、小安、小剛3名同學向記者證實,3個學年中,真正上課時間僅為12個月,“其中專業課只有3個月”。這些同學分別來自物流、計算機、市場營銷等不同專業,卻同在電子工廠做流水線普工。
此外,同學們還專門提到了“每人每學年1500元”的“國家助學金”。小羅回憶,學校老師曾讓他“簽收”一筆一學期750元的“國家助學金”,“校長說,這是助學金,一年1500元,只發第一、二年,總共3000元,到時學校會給辦一張銀行卡,統一把錢打到卡上”。
但這筆“國家助學金”在學生們“簽收”后就沒了下文,“后來學校又說過兩天會發給我們,然后又說用來抵‘生活費’,不發了”。
小羅所說的“國家助學金”是由國家財政部、教育部發放的用于鼓勵初中畢業生報考中等職業學校的資助。《中等職業學校國家助學金的具體實施辦法》(以下簡稱《辦法》)規定,國家助學金資助對象是具有中等職業學校全日制正式學籍的在校一、二年級所有農村戶籍的學生和縣鎮非農戶口的學生以及城市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標準為每生每年1500元。
在“助學金”問題上,周天華覺得“冤枉”,他承認校方的確留下了這筆助學金作為學生“生活費開支”,但他認為,“國家助學金本身就是用來資助學生的生活費開支,我們學校采取包餐制,把學生生活費都出了,2007~2008學年還墊付了751名學生150萬元,學生自己一分錢都不用出”。
記者查閱《辦法》發現,國家助學金確實“主要資助受助學生的生活費開支”,但《辦法》第9條明確要求學校為每位受助學生分別辦理銀行儲蓄卡,直接將助學金發放到受助學生手中,一律不得以實物或服務等形式,抵頂或扣減國家助學金。
周天華還針對一些學生反映的“被教官(即學校老師-記者注)打”的問題做出回應:“學校不允許打人,個別學生可能會有這樣的情況,但我不能確定。”
至于某學生向記者反映“被企業負責人打”的問題,周天華表示略有了解,但他認為這是有的學生在“夸大其詞,據我所知,可能是有的同學干活動作慢,班組長管人的語氣重了些,才發生糾紛”。
在正式委托律師以前,同學們曾給貴州省教育廳學生資助辦公室、貴陽市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局、貴陽市財政局、貴陽市教育局、貴陽市物價局分別致信投訴,除貴陽市物價局外,其他部門均未對此事做出有效回應。
貴陽市12355青少年綜合服務平臺在接到學生舉報后,表示將在了解詳細情況后作出回復。
“學生工”權益受侵犯并非個案
深圳公益律師管鐵流接手了這一“學生工”維權案例。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取證,他發現,想要為“學生工”討回公道并非易事。
“最困難的是舉證。”管律師曾經也接觸過類似的案件,他自己的親侄女就曾是一名“學生工”,只是因為在工作期間打了個瞌睡,就被實習單位“開除”,繼而被學校拋棄,“不發畢業證”,“我侄女的事情,我也沒有辦法,她小孩子,一點法律意識也沒有,什么證據都沒留下”。
同樣的問題,在貴陽“學生工”維權群體中再次出現,“那么多學生,只有一個學生有一份與企業簽訂的勞動合同副本;沒有合同,就不能把賬算在企業頭上”。
“學生工”小余告訴記者,她與企業簽過用工合同,而且據她所知,其他同學也都與企業簽過合同,“合同一式兩份,一份給企業,一份給了學校”。她清楚地記得,合同上規定“每月工資在900元到1200元之間”,但她在連續工作7個月后,卻被學校告知自己第一個學年7000多元的學雜費等尚未繳足,“只交了4000多元”。
“學生工”小羅的遭遇更加“離奇”,有一個月,他只從學校那里拿了20元“零花錢”,而他“每天至少干10個小時,平均十二三個小時,最多干過十五六個小時”。在同一個地區、相似的公司干著同樣的活兒,畢業后的小羅目前月薪已有約3000元。
要通過法律渠道“找回公道”,在管鐵流看來,主要的難點還是缺乏必要的證據支撐。
“學校可以打擦邊球,說這是‘實習’,不存在勞動雇用關系。”管鐵流覺得,目前職業教育正在相關部門的大力支持下“大膽改革”,“學校可以說這是改革中的一種嘗試,我擔心相關部門也會替學校開脫”。
北京市律師協會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目前正在關注另一樁“學生工”維權案。該中心副主任張文娟介紹,受害的貴陽“學生工”入學1周即被送往廣東一家電子廠打工,在不通風的環境下一天工作超過12小時,工作一天半后突發高燒,后被診斷為急性白血病,不治身亡,死亡時孩子尚不滿15歲。
張文娟認為,“學生工”案件即使在沒有出現人身傷害的情況下,也應當從重處罰,“對于家長,如果學校招生時虛假宣傳,不具有教學能力,大部分時間都派學生‘實習’,學生不僅可以要求退還學費,還可以要求學校對長期勞動造成身心傷害進行賠償”。